新闻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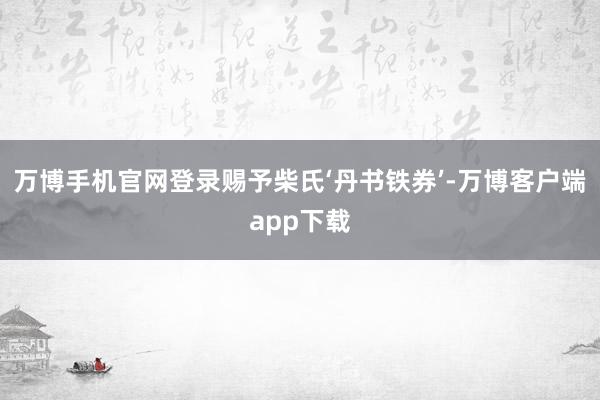
风雪夜,宫墙表里是两个世界。
宫墙外,是山呼万岁的“敬而远之”;宫墙内,是后周太后符氏抱着五岁的幼帝,在冰冷的寝殿中恭候幸运的宣判。
赵匡胤,这个也曾臣服于她丈夫的男东谈主,如今成了这宇宙新的愚弄。
当那谈威严而高大的身影出当今殿门时,符氏知谈,她不仅要保住季子的人命,更要保住柴氏皇族临了的尊容。
可赵匡胤的观点,却带着一种令东谈主颤栗的灼热。
他莫得行君臣之礼,只是慢步走向她,柔声说:“太后娘娘,臣有一事相求。此事关乎大周的血脉,也关乎娘娘的改日。”
“你休念念!”符氏牢牢护住怀中的小天子。
可是,赵匡胤接下来的话,却让她全身的血液一忽儿凝固:“娘娘,朕并非要谋您的命,而是要您的东谈主。整宿之后,您是宋朝的贵妃,大周的遗孤,才有一线但愿。”

01
正月初四,汴京城被一场出人意料的大雪遮掩,仿佛预示着一个时期的终结。
彼时,后周朝廷尚千里浸在新年喜悦的余韵中,却被一封进攻军报透顶打碎了宁静:契丹和北汉联军南下,直逼边境。
朝堂陡立乱作一团。
五岁的天子柴宗训,尚在垂髫之年,根蒂不懂得这战火意味着什么。
而垂帘听政的符太后,虽出生名门,心地坚韧,但濒临这等国之大事,亦是骤不及防。
进攻之下,群臣酌量,唯有请出殿前都点检赵匡胤,率禁军北上迎敌。
符氏坐在高高的龙椅旁,翠绕珠围,神色煞白。
她天然知谈赵匡胤拥兵自傲,功高盖主,但脚下,除了这柄最阴毒的刀,再无东谈主能抵御朔方铁骑。
“赵将军,边疆危机,社稷抚慰系于卿身。”符氏的声气带着一点压抑的嘶哑。
赵匡胤跪在殿下,身披铁甲,阵容如虹。
他的观点深重,望向符氏时,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怀,仿佛隔把沉稳宫帷,看到了她坚强外在下的脆弱。
“臣,愿为陛下,为太后,冲坚毁锐,万死不辞。”他的誓词义正辞严,却又带着一点令东谈主不安的安适。
符氏点头,赐予他御酒,亲利己他饯行。
她看着这男东谈主雄浑的身躯和遒劲的气场,心中起飞了一股深深的无力感。
她知谈,这柄刀一朝出鞘,便很难再归入鞘中。
竟然,雄师出城只是两日,便传来了惊天凶信。
陈桥驿,禁军哗变。
音问如同最凉爽的冰锥,刺穿了汴京皇城的腹黑。
符氏听到答复时,手中的茶盏“砰”地一声冲破,滚热的茶水溅湿了她的广袖,她却毫无知觉。
“赵……赵匡胤他要作念什么?”她险些是用尽全身力气才挤出这几个字。
内侍监颤抖着跪在地上:“报……报太后,赵将军在陈桥,被麾下将士拥戴,敬而远之,雄师已折复返京,不日便将兵临城下!”
“逆贼!!”符氏猛地站起身,凤冠上的珠玉摇晃,发出了逆耳的声响。
她知谈,这不是绵薄的兵变,这是赤裸裸的篡位。
她更知谈,一朝城门被攻破,恭候着幼帝和柴氏皇族的,将是难以念念象的血腥与祸害。
她坐窝召集了所有能召集的文官武将,但濒临那支刚刚平定宇宙,军多将广的禁军,所有东谈主都低下了头,眼中充满了怯生生和衰颓。
“太后,一蹶不兴,不可泰山压卵啊!”宰相范质跪地劝谏,声气悲切。
符氏的目下泄露出世宗天子柴荣的辞吐行径,阿谁主见工致的男东谈主,煞费心绪打下的山河,如今却要毁于一朝。
而更讥讽的是,赵匡胤恰是柴荣一手栽种起来的相知。
“我柴氏待他不薄,他怎么能作念出此等走嘴弃义之事!”符氏的眼泪终于滑落,但她很快擦干,脸上只剩下坚贞的决绝。
她不可哭,她是皇室的临了一谈防地。
02
大雪停了,太阳起飞,但汴京城内却笼罩着比暮夜更深的衰颓。
赵匡胤的雄师莫得攻城,而是不战而胜地干与了城内。
京城守将早就望风而降,洞开了城门。
符氏抱着幼帝,带着寥寥数名赤忱的宫东谈主,靡烂在德寿殿。
她换下丽都的朝服,穿了一身素色的深衣,却显得愈加清丽坚韧。
她轻轻抚摸着幼帝的头,小小的柴宗训还不知谈发生了什么,只是风趣地看着母亲紧绷的侧脸。
“母后,外面是不是在放鞭炮?很吵。”
符氏心如刀割,柔声哄谈:“不是鞭炮,是有东谈主在宽饶新年。”
她知谈,那不是鞭炮,那是禁军整王人齐截的脚步声,那是赵匡胤的靴子踏过御谈的声响,每一步都踏在她的心尖上。
很快,殿传闻来了喧哗声。
接着,所有宫东谈主都被完了,只留住符氏和幼帝。
殿门被推开,寒风卷着雪花涌入。
赵匡胤一身戎装,敬而远之,显得无比魁岸。
他死后随着的,是他的弟弟赵光义和相知谋士。
他莫得班师走向龙椅,也莫得急着称帝。
他只是站在殿中,观点穿透了层层宫纱,落在了符氏的脸上。
符氏昂首,观点冷如冰霜,直视着这个抗争者。
她站起身,将幼帝挡在死后,声气带着皇室特有的威仪:“赵匡胤,你可知你作念了什么?”
赵匡胤上前一步,单膝跪地,行了一个大礼。
“臣赵匡胤,拜见太后娘娘。”
这个动作让符氏微微一怔。
她原以为他会嚣张霸谈,班师晓喻拔帜易帜。
“你如今已是天子,何苦行此大礼?”符氏冷笑。
赵匡胤起身,声气千里稳:“太后娘娘,臣是得了将士们拥戴,但大周山河毕竟是世宗天子所创。臣此番转头,是为接替陛下,承担起看护宇宙的重负,并非是要行那血腥杀戮之事。”
他看向幼帝,眼中照实莫得杀意,反而带着一点哀怜。
“恭帝陛下年幼,不宜操劳国是。臣已命东谈主准备了宅邸,恭请陛下和太后娘娘移居。”
这是要“禅让”了。
符氏心头稍松。
至少,幼帝的人命暂时保住了。
“你规划怎么安置我柴氏皇族?”符氏问,口吻中带着一点阻拦置疑的强硬。
赵匡胤观点直率:“世宗天子对臣有恩光渥泽,臣不敢忘。柴氏血脉,臣必善待之,永不杀戮。这是臣对六合的誓词。”
他说的古道,但符氏却不会邋遢信服。
历史上,新朝之君对旧朝的“善待”通常只是暂时的麻木。
“白纸黑字。”符氏冷冷谈,“你夺我山河,我怎么能信你?”
赵匡胤笑了,那笑脸中带着一种掌控一切的自信。
他挥了挥手,默示所有追随退下。
德寿殿内,只剩下符氏、幼帝和赵匡胤三东谈主。
“太后娘娘,臣整宿来,是念念与您作念一笔走动。”赵匡胤的声气压低,带着只好他们二东谈主能听见的嘶哑。
“走动?”符氏皱眉。
“是,一笔能让大周皇族真确安详无虞的走动。”赵匡胤的观点再次落在了符氏的身上,不再是臣子的恭敬,而是一个男东谈主对一个女东谈主的疑望。
“娘娘,您是世宗天子的遗孀,是恭帝的生母,身份尊贵,倾国倾城。但您亦然这宇宙职权打发中,最不悠闲的变数。”
“你威胁我?”
赵匡胤摇了摇头:“不,是求娶。”

03
“求娶?”符氏险些怀疑我方的耳朵出了问题。
她以为赵匡胤会拿出金银玉帛,会拿出免死金牌,致使会建议让她交出职权,去寺庙清修。
但唯独没念念到,他会建议这种荒谬的要求。
“赵匡胤,你僭越了!”符氏怒极反笑,眼中尽是讥讽,“你如今是新朝之君,我是旧朝之太后,你还念念让我入你的后宫?你当我是什么?政治献礼吗?”
赵匡胤莫得被她的怒气激愤,他只是安适地看着她,像是在不雅察一件缜密的玉器,厚爱而专注。
“太后娘娘,您诬蔑了。臣并非要侮辱您,而是要尊重您。您是这宇宙最值得尊重的女东谈主,莫得之一。”
“尊重?”符氏冷哼,“尊重就是夺我山河,辱我清誉?”
“山河是宇宙平民的山河,大周自太祖郭威以来,也履历过血腥。如今华夏需要一个强有劲的政权来收尾五代十国的乱局。”赵匡胤口吻坚决,带着君主的自信,“而至于清誉,臣从未念念过浑浊您。臣要娶您,光明正地面娶您,立您为妃。”
“白天见鬼!”符氏坚忍拒却。
她乃是正宗太后,岂能屈身于弑君篡位者的后宫?
这不仅是她个东谈主的耻辱,更是对所有柴氏皇族的污辱。
“娘娘,请听臣把话说完。”赵匡胤的声气放缓,带着一点诱骗东谈主心的魔力,“您以为,臣只是单纯地看上了您的好意思貌和身份吗?”
“难谈不是吗?”
“天然不是。”赵匡胤走到殿中的桌案前,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,“娘娘,您比谁都了了,如今的汴京城并非铁板一块。城中除了效忠于臣的新军,还有大量后周的旧臣、旧将。他们口头臣服,内心却对柴氏皇族怀有赤忱。”
符氏心头一动,但莫得接话。
“如果您只所以太后的身份隐居,那些旧臣旧将,势必会将您视为反抗的旗子。”赵匡胤观点敏锐,直刺符氏的内心,“他们会打着‘复周’的口头,聚拢力量,发动叛乱。”
“那与我何关?”
“与您无关吗?”赵匡胤提升了声气,“一朝叛乱发生,无论成败,柴氏血脉都将成为首要的葬送品。娘娘,您真以为,臣能容忍一个潜在的威胁存在于京城内吗?”
符氏神色骤变。
赵匡胤说得没错。
她淌若连续保持太后身份,那些忠于柴氏的东谈主一定会围绕她张开行为,而新帝为了巩固职权,势必会遴选雷霆期间,届时,幼帝将首当其冲。
“赵匡胤,你这是逼我!”
“臣是在救您,救您的孩子。”赵匡胤咨嗟一声,带着一种治服者的暖热,“臣娶您,即是向宇宙宣告,大周与大宋还是水乳交融,柴氏与赵氏已成姻亲。您的身份,将从‘旧朝太后’,相同为‘新朝贵妃’。”
“如斯一来,那些心胸不轨的旧臣,便失去了呐喊力。谁敢再打着‘复周’的旗号?他们反抗的,将不单是是臣,更是您的眷属,您的采纳。”
他将所有的政治压力,精巧地升沉成了符氏个东谈主的保护神。
符氏心绪翻滚。
她不得不承认,赵匡胤的提议,诚然充满了污辱和要挟,却是保全季子最佳的格式。
可她怎么能继承?
她是大周的国母,是世宗的妃耦。
“我淌若应允,宇宙东谈主会怎么看待我?史册会怎么记录我?”符氏声气颤抖,这是她当作政治东谈主物临了的费心。
赵匡胤笑了,笑得绝顶霸谈。
“宇宙东谈主?史册?太后娘娘,这宇宙,从今往后,由朕说了算。史册,也由朕的东谈主去写。”
他走到符氏眼前,俯身,带着遒劲的压迫感。
“娘娘,您不是为我方而活,您是为柴氏血脉而活。您需要一个有余遒劲的靠山。而这宇宙,只好朕,能作念您的靠山。”
04
符氏站在原地,与赵匡胤的观点交汇,空气中充满了炸药味和一点难以言喻的隐隐。
她能感受到他身上懒散出的遒劲荷尔蒙,那种治服宇宙的霸气,带着粗砺的迷惑力。
但这种迷惑力,此刻对她来说,却是致命的毒药。
“你说的这些,不外是你的说辞。我若不从,你难谈就会放过我柴氏吗?”符氏指天画地地揭穿了这层子虚的面纱。
赵匡胤莫得否定。
他直起身,散步到窗边,看着宫墙外逐步暗下来的天色。
“娘娘,臣不会对恭帝作念什么。臣不错立誓,赐柴氏铁券丹书,保其世代高贵。”
他顿了顿,口吻变得冰冷:“但娘娘,您必须显然,一个王朝的陨命,总需要一些葬送。如果我不可用最和平的格式收尾这一切,那就只可用最血腥的格式。”
“你威胁我!”符氏的声气提升了八度,带着压抑的怒气。
“不,臣是诠释事实。”赵匡胤转过身,眼中带着一点训诫,“娘娘,您是颖慧东谈主。您也知谈,旧臣中,有东谈主还是开动撺拳拢袖。他们不是忠于柴氏,他们只是不欢跃职权旁落。”
“如果他们发动叛乱,我该怎么向将士们交代?我不可让我的将士们流血,去平定一场本不该发生的叛乱。”
他的语言,字字诛心。
符氏知谈,一朝简直发生兵变,赵匡胤会绝不海涵地将所有与柴氏相关联的东谈主削株掘根,以绝后患。
届时,柴宗训即便有免死金牌,也难保万全。
“我若嫁你,那些旧臣会怎么看我?”符氏声气低千里,充满了横祸。
“他们会看您是个为了保护孩子而作念出葬送的伟大母亲。”赵匡胤嘴角微扬,涌现一抹掌控全局的笑脸,“您将成为大宋的贵妃,但您更是恭帝的生母。您在宫中,恭帝在宫外,这即是最佳的均衡。”
他走近她,声气放得更轻,带着一种令东谈主无法抗拒的魔力。
“娘娘,您是不菲的凤凰,不该在甩掉的宫殿里,守着一个还是逝去的王朝。您应该站在最高的枝端,俯视宇宙,才能真确地坦护您念念保护的东谈主。”
符氏闭上眼睛,脑海中闪过了无数念头。
反抗?
她拿什么反抗?
她死后是心虚无力的文官,是未成年的幼帝。
赵匡胤手捏宇宙最精锐的部队。
清修?
她淌若清修,失去了职权中心的坦护,柴宗训随时可能被有时“病逝”。
结亲?
这是辱没,但亦然独一的生路。
她猛地睁开眼,观点中带着已然:“如果我理财,你怎么保证,柴氏血脉永世安康?绝顶是恭帝,你怎么保证他能安全长大,不受你子嗣的威胁?”
赵匡胤笑了,他知谈,她还是动摇了。
“娘娘,这即是整宿咱们必须详谈的重要。这不单是是政治结亲,更是职权交换。”他压柔声气,指向了窗外飘渺的夜空,“这漫漫永夜,足以让咱们将所有条目,一字一板地敲定。”
符氏深吸连气儿,心中掀翻了滔天巨浪。
她知谈,整宿之后,她将透顶从后周的太后,造成大宋的贵妃,她的名字,将与赵匡胤紧密地酌量在通盘,无论清誉或骂名,都将陪同她终身。
她看向死后的幼帝,孩子还是依偎着她睡着了。
为了这孩子,她必须作念出采纳。
05
符氏缓缓坐下,动作优雅,但躯壳的每一寸肌肉都绷得牢牢的。
“好,赵匡胤。我听着。但你必须显然,我不是一个任东谈主搬弄的女东谈主。你念念要我,不错。但你必须付出有余大的代价。”她的口吻规复了太后的威严,那是多年身居高位养成的气场。
赵匡胤抚玩地看着她。
他要的,恰是这种坚韧。
一个心虚的女东谈主,无法成为他踏实山河的基石。
“娘娘请说。只消臣能作念到,绝不拒接。”
“第一,恭帝柴宗训必须被尊为‘郑王’,享受亲王待遇,食邑三万户,永镇一方。且不可调离封地,以保安全。”符氏建议了第一个要求,将幼帝透顶从职权中心剥离,以幸免改日被疑忌。
“可。”赵匡胤点头,这在他意象之中。
“第二,你必须下旨,赐予柴氏‘丹书铁券’,且本体须昭告宇宙,永不杀戮柴氏子孙。若后世子孙各异此誓,则不得好死。”符氏强调了誓词的公开性和漫骂性。
赵匡胤眼中闪过一点不易察觉的称许:“可,臣会亲自撰写此誓,藏于太庙,令后世子孙难忘。”
“第三,”符氏深吸连气儿,这是最重要的一条,“我诚然嫁你,但你必须保证,我眷属东谈主,绝顶是我的兄弟们,不得因柴氏陨命而受到瓜葛。他们必须得以保全,连续为官,好像退隐,由他们我方采纳。”
赵匡胤千里吟了一下。
符氏的兄长符彦卿是后周名将,势力浩大。
保全他们,意味着他要容忍一股旧势力连续存在。
“臣不错保证,符氏眷属的体面。但若有东谈主心胸异志,妄图谋反,臣将不吝血洗。”赵匡胤口吻坚决,划清了底线。
“我自会拘谨族东谈主。”符氏应允。
她建议的三条,都是为了确保柴氏和符氏眷属的安详。
但赵匡胤知谈,真确的挑战,还在于怎么让这位骄横的太后心甘宁愿地放下一切,成为他的女东谈主。
“娘娘,您建议的条目,臣都理财了。但臣也有一个条目。”赵匡胤的观点变得深重,带着一种扰乱性。
“你说。”
“您必须在三日之内,以‘符氏’的口头,而非‘太后’的口头,公设备布诏书,标明您是心甘宁愿嫁给臣,并赞赏臣登基是适合天命。”
这才是最毒辣的要求。
这不仅是结亲,更是要符氏亲手糟蹋后周的正当性,为他的篡位正名。
符氏的神色变得极其出丑。
这比杀了她更疼痛。
“赵匡胤,你太过分了!”
“娘娘,这是必须的。”赵匡胤口吻安适,却阻拦置疑,“您若只是被迫,那些旧臣依然会视您为‘东谈主质’,视您的诏书为‘要挟’。只好您心甘宁愿,才能透顶断交他们的幻念念。”
他上前一步,气味险些喷洒在她的脸上。
“您可知谈,就在您与臣赈济的此刻,城中有些许东谈主在盯着这座宫殿?他们不在乎山河社稷,他们只在乎我方的昌盛高贵。他们渴慕看到您反抗,渴慕看到流血,这么他们才有契机趁乱而起。”
赵匡胤的声气骤然变冷,带着一点狠厉。
“臣刚才说了,臣承诺善待柴氏。但臣也必须清除所有阻截新朝的势力。如果娘娘不协调,臣将无法分别,谁是真确赤忱的旧臣,谁是心胸不轨的乱党。”
他俯下身,在符氏耳边低语,声气如同低千里,带着致命的诱骗和威胁:

“娘娘,您是这宇宙临了一谈对于柴氏的樊篱。一朝您倒下,汴京城中所有与柴氏沾亲带故的东谈主,都将失去坦护。到时候,可就不是绵薄的‘清退’了,而是——血流漂杵。”
他直起身,眼中闪过一点森冷的冷光。
“史官们正在恭候。他们要看,您所以示寂的烈女身份被载入史册,还所以新朝贵妃的身份,连续活下去,并保护您念念保护的一切。”
“娘娘,是采纳尊容,如故采纳糊口?整宿,您必须给臣一个谜底。”
符氏感到一阵昏迷,她知谈,她还是走到了峭壁边上。
赵匡胤不仅要她的躯壳,要她的身份,更要她的灵魂,让她成为他政治正当性上最完满的注脚。
她深吸连气儿,眼底充满了辱没和不甘,但为了季子,为了眷属,她知谈我方别无采纳。
“赵匡胤,我理财你。”符氏的声气带着一种破灭的已然。
赵匡胤景观地笑了,但他的下一步动作,却让符氏再次战抖。
他莫得坐窝起身,而是伸脱手,轻轻地,却又极具力量地,捏住了符氏的手腕。
“娘娘,您是世宗天子的妃耦,是太后。您淌若屈从,宇宙东谈主会认为您是被迫的。臣不可让您带着这种屈身入宫。”
他缓缓地,将她从座位上拉起,观点灼灼,带着一种治服者的霸谈和一种无法抗拒的暖热。
“臣要让您心甘宁愿。臣要让您知谈,嫁给赵匡胤,比作念任何王朝的太后,都愈加荣耀。”
符氏只觉班师腕上传来酷暑的温度,她试图挣脱,但他的力量遒劲到让她动掸不得。
殿外的雪又开动下了,避讳了所有阅览的观点。
符氏知谈,这不单是是职权的较量,更是她与赵匡胤之间,一场关乎幸运的较量。
她看到了赵匡胤眼中那团烧毁的火焰,她感到我方的尊容、她的曩昔、她所有的骄贵,都将在这漫漫永夜中,被透顶溶解。
06
那夜,德寿殿中的灯火摇曳,却从未灭火。
史官们在殿外等候,慌乱而欣喜。
他们知谈,殿内正在演出着决定新朝幸运的重要一幕。
他们臆想着,符太后是会自刎示寂,如故会被新帝逼迫就范。
莫得东谈主敢念念,她会“心甘宁愿”。
殿内,符氏被赵匡胤牢牢捏入辖下手腕,她的挣扎在完全的力量眼前显得挥霍来回。
“放开我!”符氏的声气压抑而震怒。
赵匡胤却只是将她带到了殿中央,他莫得急于行那男女之事,而是作念了一件出乎符氏意象的事情——他脱下了身上那件象征着君主身份的黄袍。
那黄袍,是陈桥兵变时,将士们披在他身上的。
如今被猖狂扔在了地上,涌现了他内部那件深色的燕服。
“娘娘,您说我是僭越,是谋逆。但您可知,我为何能在彻夜之间,让所有汴京城安适下来?”赵匡胤的声气不再带着要挟,而是带着一种对宇宙大势的深入明察。
他莫得给她回话的契机,连续谈:“因为我能给这宇宙,带来和平与悠闲。您贱视我这个行伍出生的武夫,合计我鄙俗不胜。可您更应该看到,在我死后,是数百万饥寒交迫的平民,是渴慕安宁的将士。”
“世宗天子的确主见工致,但他操劳国是,最终英年早逝,留住了您和五岁的幼帝。娘娘,您合计,在契丹和北汉的铁骑眼前,一个五岁的孩子,能守住这万里山河吗?”
符氏千里默了。
这是她心中最深的痛。
“您不可,那些旧臣也不可。”赵匡胤走到她的眼前,观点如同鹰隼,直视她的内心,“他们只念念着职权倾轧,念念着如安在这浊世中多捞一笔。他们不会为大周而死,他们只会为我方而活。”
赵匡胤莫得像其他天子那样,只用职权和暴力治服女东谈主。
他用的是“谈”,是“势”。
“娘娘,您的好意思貌和您的身份,是您最大的火器,亦然最大的危险。您若嫁我,您即是大宋的贵妃,您和您的孩子,都将享受大宋的昌盛。您若不从,您即是大周的余孽,是挑动叛乱的首恶。”
“您以为,我为何要将那份‘丹书铁券’昭告宇宙,藏于太庙?”赵匡胤的声气带着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沉着感,“因为我是在向宇宙宣告,我所以仁德取代暴政,我给了前朝皇族最大的体面。这体面,不是我给柴氏的,而是我给您的。”
“我需要您来评释,我的新朝是适合民意,是和平过渡。”
符氏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。
她不是被他的威势吓哭,而是被他展现出的庞杂政治样式所涟漪。
她倏地毅力到,我方所谨守的“尊容”,在宇宙百姓眼前,是何等的微不及谈。
“我淌若嫁你,怎么濒临世宗天子?”符氏抽陨涕噎着问。
赵匡胤走到她的死后,双手轻轻搭在了她的肩膀上,动作带着一种令东谈主心悸的暖热。
“世宗天子淌若泉下有知,他会感谢您。感谢您保全了他的血脉,感谢您以一己之力,换来了宇宙的安定。”
“他待我有恩光渥泽,我敬他如兄长。您嫁给我,是连续作念您未完成的责任——坦护柴氏。娘娘,您不是在效劳,您是在延续。”
赵匡胤的语言,透顶击溃了符氏临了的心思防地。
他把所有的辱没,都包装成了“大义”和“株连”。
他让她信服,这桩政治结亲,不是她对旧朝的效劳,而是她对季子和宇宙最大的赤忱。
“我……我若理财,你当真能保柴氏永世不杀?”符氏的声气带着深深的困窘和息争。
“我以赵氏列祖列宗的口头发誓。”赵匡胤的声气变得无比庄重。
那一刻,符氏终于显然,她还是输了。
不是输给了武力,而是输给了赵匡胤的政治智谋和君主之气。
她缓缓回身,抬早先,眼中已然莫得泪水,只好一种浴火更生的坚韧。
“好,赵匡胤。我嫁你。但你要记着你整宿对我的所有承诺。”
赵匡胤眼中闪过一点狂喜,但很快被他压下。
他知谈,真确的治服,才刚刚开动。
他抬手,轻轻拂去了符氏面颊上的泪痕。
“娘娘,您作念了一个最理智的决定。”
他不再评论政治,不再评论山河。
他只作念了一件,让符氏透顶放下防护,心甘宁愿的事情。
他拥抱了她。
这个拥抱,带着树立沙场的铁血之气,带着君主非常的占有欲,却又带着一种对她葬送的相连和尊重。
他莫得坐窝索求,而是用最暖热的格式,让她感受到,她不再是阿谁孤独无援的太后,而是一个被新帝防止和渴慕的女东谈主。
那彻夜,与其说是新帝对旧太后的治服,不如说是新朝对旧朝的吸纳。
符氏的息争,换来了大宋山河踏实的基石。
而赵匡胤对她的尊重和承诺,也让她从政治葬送品,造成了新朝的定海神针。
她知谈,她作念出了一个能让柴氏活下去,并活多礼面的采纳。
07
第二天清早,太阳照常起飞,但汴京城却迎来了透顶的相同。
符氏的寝殿内,赵匡胤早已离去,但他留住的,是那份用朱砂亲笔写下的承诺书,以及一份拟好的诏书草稿。
诏书本体,恰是符氏要以“符氏”的身份,而非“太后”的身份,向宇宙东谈主宣告的。
符氏看着那草稿,字字句句都充满了对赵匡胤“适合天命”、“仁德宽厚”的赞赏,以及她对柴氏幼帝“年幼不胜重负”的无奈。
她知谈,一朝这诏书发出,她将透顶断交所有旧臣复辟的念念念。
她将成为新朝的协谋,新帝的羽翼。
当内侍总管小心翼翼地前来讲述时,符氏面色安适,莫得一点踌躇。
“去,按这草稿,拟成稳重诏书,以最快的速率,昭告宇宙。”她的声气带着一种压倒性的安适。
她已作念出采纳,便不会再回头。
诏书一出,汴京城内哗然。
好多本来还心存幻念念的旧臣,透顶衰颓。
他们本以为符太后会是抵抗到底的象征,是他们聚拢的旗子。
欺压,这位太后不仅莫得反抗,反而主动为新帝站台。
“太后娘娘,是为了保全柴氏啊!”有东谈主悲愤杂乱,但更多的东谈主,采纳了千里默。
连太后都采纳了归顺,他们还有什么事理去反抗?
赵匡胤的政治手腕,在此刻展现得长篇大论。
他莫得流一滴血,却剖判了旧朝所有的抵抗意志。
接着,赵匡胤发布了第二谈旨意:尊后周恭帝柴宗训为“郑王”,并速即将其移居至他处,辨别职权中心。
同期,他达成了对符氏的承诺,将那份“丹书铁券”的本体公之世人,并亲自若太庙中立誓。
第三谈旨意,即是迎娶符氏。
他莫得以“纳妃”的口头,而所以无际的“迎娶”之礼,将符氏接入宫中,封为“贵妃”,地位仅次于皇后。
这一系列动作,让宇宙东谈主显然:新帝对旧朝,是宽宏的,是结亲的,是和平过渡的。
但事情并未完全收尾。
诚然符氏的息争带来了口头上的和平,但那些真确闭塞的“柴氏旧眷”——那些非符氏眷属,而是与柴氏有深重利益纠葛的旧臣,依然热血沸腾。
他们暗里约聚,大骂符氏是“朱颜祸水”,是“顽抗卖国”。
赵匡胤对此心知肚明。
他在恭候,恭候他们涌现马脚。
符氏入宫后,坐窝发扬了她当作旧朝太后的影响力。
她通过我方的渠谈,很快掌捏了那些不平者的名单。
在一次与赵匡胤的密谈中,符氏将一份名单交给了他。
“这些东谈主,是真确的乱党。他们并非忠于柴氏,而是念念借柴氏的口头,谋取私利。他们若不除,大宋难安,恭帝也难安。”符氏口吻安适,莫得涓滴的哀怜。
她还是从一个被迫的受害者,透顶相同为新朝的政治盟友。
她知谈,要保护我方的孩子,就必须亲手斩断那些谬误的“赤忱”。
赵匡胤看驰名单,脸上涌现了景观的笑脸。
“娘娘竟然是深明大义。”
“我所求的,只是一个安详的改日。”符氏回话。
08
赵匡胤的清洗行为,悄无声气,却又迅疾无比。
他莫得风风火火地进行血洗,而是给与了最抽薪止沸的格式——抢劫职权,充军辽远。
最初被处置的,是那些在陈桥兵变中莫得实时归顺,反而试图组织抵抗的旧将。
他们被以“迟延军机”、“贪腐纳贿”等罪名,速即澌灭兵权,流配充军。
接着,是那些执政堂上阴奉阳违的旧臣。
赵匡胤以“冗官过多,需精简朝堂”的口头,将他们或贬为平民,或调离京城,永不叙用。
最重要的是,赵匡胤透顶赶走了后周的旧禁军,将其打散重组,融入新军之中,并栽种了一批新的将领,确保部队的完全赤忱。
所有经过,不时了约一个月。
当风云平息时,汴京城内的“柴氏旧眷”,还是透顶被清空。
那些真确忠于柴氏,但莫得反抗之心的旧臣,则被符氏保了下来,他们得回了体面的退隐生活。
史官们不雅察着这一切,担惊受怕。
他们发现,新帝赵匡胤的期间,比以往任何一次拔帜易帜都要松弛。
他莫得杀戮,却达到了比杀戮更透顶的成果——去势。
他让所有与旧朝关系的势力,透顶失去了影响新政的才能。
而这一切的背后,都有符氏的影子。
符氏在后宫中的地位,随着她对赵匡胤的匡助,变得越来越踏实。
她诚然是“贵妃”,但她对政治的明察和观点,让赵匡胤对她越来越信任。
她不仅是赵匡胤的女东谈主,更是他政治上的贤爱妻。
赵匡胤达成了他的承诺。
他亲利己符氏的季子柴宗训修建了豪华的郑王府,并派去最精锐的侍卫保护。
他确保了柴宗训的练习和生活,让他以一个亲王的身份,安适地长大。
符氏的心,渐渐地安适下来。
她从一开动的辱没和不甘,逐步继承了试验。
她知谈,她用我方的婚配,为季子和眷属,买了一个太平盖世。
赵匡胤对她的瞻仰,也并非只是政治造假。
他抚玩她的智谋和坚韧,也崇拜她为保护眷属所作念的葬送。
“娘娘,”有一次,赵匡胤在批阅奏折时,昂首对符氏说,“您是朕见过的,最懂得弃取的女东谈主。”
符氏只是浅浅一笑,眼中却带着一点自嘲:“陛下谬赞。不外是被幸运推着走完了。”
但她知谈,她还是不再是阿谁任东谈愚弄割的旧朝太后。
她用我方的智谋和葬送,在新的职权结构中,找到了我方的位置。
她成了大宋的贵妃,亦然柴氏最遒劲的保护者。
09
时期缓缓荏苒,大宋王朝逐步踏实。
符氏的身份,从也曾的“后周太后”,透顶转造成了“大宋贵妃”,成为了赵匡胤后宫中一谈非常而尊贵的存在。
她莫得像好多东谈主预期的那样,成为一个深宫怨妇,而是展现出了她当作政治家的天禀。
她参与了对后周旧制改造的建议,匡助赵匡胤平稳地过渡了好多计策。
她的存在,自身就是大宋“仁德治宇宙”的最佳评释。
史官们在记录这段历史时,不得不小心翼翼。
他们不敢说起符氏当初的挣扎和赵匡胤的要挟,只可侧重于记录“符氏太后深明大义,主动禅让,并心甘宁愿嫁入宋宫,以保宇宙太平”的“好意思谈”。
史册上,将那场结亲描写得充满和谐与政治远见。
可是,那些切身履历过陈桥兵变的老臣们,心中都了了,那场“彻夜”的交锋,远比史册上记录的要惨酷得多。
那不是风花雪月,而是刀光剑影的心思博弈。
符氏的息争,换来了所有柴氏眷属的“不杀”之约,这份承诺,最终被赵匡胤刻在了石碑上,藏在太庙之中,警示后世子孙。
这是符氏用她的尊容,为柴氏争取到的最高保险。
几年后,大宋山河踏实,赵匡胤开动入辖下手和谐宇宙。
符氏在后宫中,依然保持着她的威严和体面。
她从未健无私方的出生,也从未健无私方的责任。
她按时去阅览还是长大的郑王柴宗训,看着他在封地中安详过活,她的内心才感到一点慰藉。
柴宗训对她,永恒保持着孺慕之情,但他对政治却莫得任何风趣,这让符氏感到宽解。
一个莫得贪念的前朝皇子,才是最安全的。
在符氏的奋力下,符氏眷属也得以保全,他们中的杰出人物,依然活跃执政堂之上,成为了王人集新旧势力的一股要紧力量。
可是,代价是千里重的。
那些也曾在大周朝堂上推波助澜的“柴氏旧眷”,那些不肯归顺的忠臣,那些心胸叵测的乱党,都还是在赵匡胤的铁腕下,隐匿得荡然无存。
他们莫得流血,却被透顶从职权的舞台上抹去。
汴京城内,再无东谈主敢公开评论“复周”之事。
所有东谈主都显然,后周还是透顶成为历史,而符贵妃,就是这段历史的终结者。
10
深夜了,符氏站在宫殿的窗前,望着窗外汴京城的灯火。
如今的汴京,还是是大宋的京城,繁华依旧,但统率者还是换了。
赵匡胤从死后拥住了她,他的气味带着树立后的困窘,却又带着君主的关心。
“娘娘,在念念什么?”
“在念念陈桥兵变的那彻夜。”符氏的声气很轻,带着一点远处的咨嗟。
“那彻夜,你逼我太紧。”
赵匡胤笑了,将下巴抵在她的发顶:“只好逼紧了,你才能作念出最正确的采纳。朕需要的是一个心甘宁愿的盟友,而不是一个被囚禁的怨妇。”
“你赢了。”符氏承认。
“咱们都赢了。”赵匡胤矫正谈,“你赢了柴氏的安宁,朕赢了宇宙的太平。”
他转过她的身子,观点深重而复杂:“朕知谈,娘娘心中永恒有怨。但娘娘,你已是这宇宙最尊贵的女东谈主之一,你为你的孩子和眷属,作念出了足以被后世称颂的葬送。”
符氏靠在他的怀里,感受着这个男东谈主的遒劲。
她知谈,无论史册怎么记录,她与赵匡胤之间的关系,都将是历史上最复杂的一页。
她从一个一火国太后,造成了新朝贵妃,她用她的婚配,完成了对旧朝的终极保护。
史官笔录:
公元 960 年,大宋开国。
宣懿符皇后(恭帝之母符氏),深明大义,主动归顺,赞赏太祖适合天命。
太祖感其德行,纳为贵妃,并赐予柴氏丹书铁券,永不杀戮。
那夜之后,汴京城内再无柴氏旧眷。
所有企图借机闯祸的旧臣,皆被新帝以雷霆期间清除。
符贵妃以一己之力,换得了柴氏的安宁,幸免了血腥夷戮。
她成了赵匡胤踏实山河的重要,也成了柴氏血脉的看护神。
那段历史的真相,被深深地埋藏在了时期的长河中。
只好少数亲历者知谈,那不是一场绵薄的结亲,而是一场关乎死活、尊容与宇宙的政治博弈。
而符氏,最终采纳了放下尊容,拥抱宇宙。
(全文完)
创作声明:本文为凭空创作,请勿与试验关联。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,部分图片非着实图像万博手机官网登录,仅用于叙事呈现,请细察。

